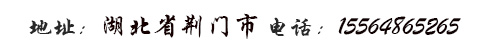乡情散文生产队里捡麦穗
|
北京医院手足癣 http://m.39.net/baidianfeng/a_8833423.html 乡情散文:生产队里捡麦穗 文:杨晓光 上世纪七十年代,正值“吃小家饭,干大家活”走人民公社化道路的年代。在昌黎县晒甲坨农村老家,每年夏收大忙一开始,我就读的四村小学都要放十天“麦秋假”,各班级学生回到所在生产队,参加集体夏收劳动。开学前,由所在生产队开出“劳动表现”鉴定,带回学校,作为评比“三好红小兵”的依据。 对当年的农民社员而言,粮食是命,颗粒归仓,是一种自觉的认同和统一的行动,没有谁要求这样做,每个社员都能做到主动去做。我们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,则每天跟着割麦的大人一起出工,胳膊上挎个篮子,在割完拉走麦子的地块,捡拾地上遗落的麦穗。将捡到的麦穗揪下秸秆,篮子里只留下黄橙橙的麦穗。收工时,我们挎着装满了麦穗的篮子,将麦穗送到生产队的场里,由队会计过秤、记工分。那时我们的思想觉悟都很高,没有一个把麦穗带回家的。对于正值少年儿童的我们来说,捡麦穗无疑是辛苦的,一天到晚和大人们一样,头顶日头晒着,地下暑气蒸着,浑身上下火烧火燎的,刚刚割过的麦地里,稍有不慎还会被尖利的麦茬划破脚踝,简直又疼又痒。捡麦穗也是有益的,我们亲眼看到了大人们劳动的辛苦,获得收成的不容易,同时我们也从小磨练了意志,淬炼了品质,晒黑了我们的皮肤,炼红了幼小的心灵。当年我没少参加生产队劳动,拾过麦子,捡过豆子,拾过高梁,捡过苞米,刨过白薯,拣过白菜帮。 在麦田,大人们挥汗如雨,挥舞着镰刀,麦子成片地倒下,被后面的人利利索索地捆扎好,装上大车,装满的车辆像一座座小山一样,在田间路上缓慢移动,清脆的鞭声响处,一辆辆麦车驶向了打麦场。我们只顾了低着头,在空旷的麦田寻觅,仔细瞅着地面,寻找被遗漏的零散的单株麦子,哪怕一棵麦穗也要拾捡到篮子里。越临近中午,日头照射得越毒辣火热,令人想起课堂上背过的一句古诗:遥看瀑布挂前川。只不过这是阳光的瀑布。大多数孩子都歪歪扭扭地戴着一顶大人不用的旧凉帽,除了帽檐底下一圈阴凉,整个田野都晃得白茫茫的,展眼望去,远处的麦茬似乎在蒸腾的暑气中隐约晃动,看得人眼前一片迷离。 为了给自己打气鼓劲,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,我们开始大声地唱歌,“我是公社小社员呐,手拿小镰刀呀,身背小竹篮啊。放学以后,去劳动。割草,积肥,拾麦穗,越干越喜欢……”我们一边在田野上更加欢快地捡拾麦穗,一边放声歌唱。似乎忘记了疲劳,也忘记了炎热,把饥渴和疲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 歌声惹得麦秋的飞腿蚂蚱(学名叫中华稻飞蝗)“啪啪”地振翅飞掠过头顶,露出第二层粉红的翅膀,格外让我们眼馋。多想捉住这一只只飞掠的蚂蚱,扔进灶坑烧着吃啊,那该是满肚子鼓鼓囊囊的黄籽吧,多香啊!无奈,这种蚂蚱好像没有起落架的飞机,又像掐断腿的蜻蜓,只看见它们从空中飞过,只听见“啪啪”拍打翅膀的声音,很少见到它们落下来。就算落地一小会,也像蜻蜓点水,颠颠脚再次振翅高飞。 度过繁忙的麦假,开学后的几天里完全不必收心,学校搞勤工俭学,还要组织师生拾捡麦穗,这第二遍的拾遗,仍然颇有斩获的。前几天在地里毫不费力就能拾捡满满一篮子,现在每人能强巴力也才拾捡半篮子,但是积少成多,全体师生拾捡的麦穗积攒到一起,那也是十分可观的收获。学校用我们拾捡麦穗换来的收入,作为秋季新学期开学的书本费。 “捡穗日当午,汗珠滴下土”。当年默写课文,因“篡改”古诗词被扣分的情景,以及汗流浃背捡麦穗的“公社小社员”劳动场面,在我记忆里依然那样清晰,就像发生在昨天的故事,又像重新播映的电影胶片,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。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,若侵权联系删除。欢迎文友原创作品投稿,投稿邮箱 qq.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oyae.com/dygj/7669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为什么不爱早起的人,脾气都不太好
- 下一篇文章: 晨读bull年度检察机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