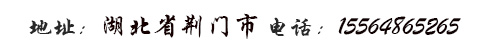寇波浪乡野记忆
|
北京中医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://m.39.net/baidianfeng/index.html 点上方↑"家在盩山厔水间"免费订阅本刊 我想借着我的笔,为我、以及那些经历过乡野生活的人们,留下些淳朴、自然、美好的乡野记忆...... 水 我今生注定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命理家告诉我,我是水命,而且是大海水命;根据西方星象学来说,我属于天蝎座,亦为水相星座;而我出生的地方虽不似江南处处有水,大河小河却也多见。命中多水者多智,我的水也太多了,可能物极必反,把脑袋冲坏了,所以我并没有多智,而是多愚。 一、屋后小河 我家在村子东南角,是第一户。屋子坐南朝北,一条小河从屋后墙外自西向东、在东南角又折向北流,绕院落两面。我的家就像是这河流的臂弯里的孩子,赖在母亲的怀抱中。 当我刚过完满月,肯定我的母亲或者我的奶奶已经抱着我,在这条小河边一边哼着儿歌,一边逗着我笑,我那时肯定已经看到了清凌凌的河水与岸边的素淡的野草小花。 我叫“波浪”。也许是巧合,也许是我的父母某天在后墙外淘米洗菜的时候,看着这水流中欢快的浪花而心念一动,取了这个名。而这瞬间的起心动念,无形中又给我那多水的命运里增加了水分。 渐渐地,我能走能跑了,这小河便成了我的乐园。 开始跟随大人走出后院的门,看着他们在清泠的水中淘小麦。先把口袋里的麦子倒进筛子,然后放进水中左右攧榥,或者手握筛子的两边在水中摇着圈子,这样可以使沙土沉入筛底,使麦子的壳上浮,大人们用一种叫做“笊篱”的灶具,撇清浮起来的麦壳和些许小杂物,最后把淘净的麦子倒在事先铺好的竹席上,摊开晾晒。我则坐在竹席的一个角上玩耍,有时稚嫩的小手会抓起竹席上的麦粒乱扔一气,大人看到,赶紧掰开我的小手,掏净我手中的麦粒,假装生气的责难:“哎,小娃不敢洒坏,再洒坏,就甭想吃馍了。”我一见大人凶我,扔麦粒的手就更来劲了,大人看没法子,就腾出一个人,把我带别处去玩。 带我去别处的这个人,大多时候都是大我七岁的姐姐。我姐引着我,沿着河岸小路往上走,一路走,一路采着野花,一路哼着只有她自己才明白的调调,时不时把漂亮的花插在她头上,把不好看的插在我头上。等这一路下来,我的头上和她的头上都开满了花。她还会用狗尾巴草扎成动物的形状,在我跟前晃来晃去,就是不给我玩,我每每追着她讨要。后来,我要她教我狗尾草扎动物的绝活,可惜的是,到现在我都没能学会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慢慢长大、懂事,出来不再要大人照看,自己推开后院的门,一个人玩耍。小河其实并不宽,两岸距离最宽处也就五米左右,水深也不过一米,窄的地方还不到两米,水深不过两尺,我觉得唤作小溪,更为恰当。河水悠悠中打着旋,水纹细腻而短小,只在狭窄一些的地方发出淙淙声,水色清澈,能见水底细软的泥沙和柔嫩的水草,还有水中一群一群的游鱼和小虾,鱼虾虽都不大,但个个活泼、欢快、有精神。 河的对岸就是庄稼地,边上都长着一排排的树。这些树,农村很常见,无非榆、柳、椿、槐,榆树有榆钱,仲春嫩黄甜粘,可做榆钱饭;槐树有槐花,初夏可见一树白玉,香甜可口,可做麦饭;椿树出香椿,我爷爷常掰下椿芽,为我解馋。此三者,在农村当时,可算得上是顶好的吃货了,而我一直对此不感兴趣。 我独喜爷爷菜地边不知多大年岁的那棵歪柳,每当春到,柳枝萌芽,条缕舒展,随意春风。我则折来较粗而没有档节的柳枝,用手扭几下,将柳枝的皮和柳枝的干的粘连扭开,抽出柳枝干,只剩一截完整的柳枝的皮,然后坐在岸边的青草上,用剪刀把柳枝的皮裁成合适的几段,拿出任一段的一端,用手的拇指和食指掐去外表较厚的皮,只留下内里薄薄的一层,顺着掐痕捏扁,然后把捏扁的一段放进嘴里,就可以吹出调调了,我们管这样做成的哨子,叫做柳哨。据我的经验,做哨子最好的材料还是柳枝好,因为柳枝的皮外边光滑,而且柳枝的皮含在嘴里不仅不苦,还有淡淡香味,这就要比杨树、槐树等树的皮好得多。哨子发出的调子也是因哨子的粗细长短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,短而细的哨子,吹出的调子短而清脆;短而粗的哨子,吹出来的调子短而洪亮;细而长的哨子,吹出来的调子悠扬而略欠清悦;粗而长的哨子吹出来的调子厚重而悠远。 做好了柳哨,我一边吹着,一边欣赏着柳树在水中的倒影。风吹柳枝拂动,柳枝拂动,柳树在水中的倒影就晃动,水本来就在流动,而水里的鱼虾在水中的柳影里游动,虽然都没有声音,却相应成趣,生机盎然,潜藏着丰富的生命力。 我童年的很大一部分时光都是在河边度过的,小河不仅是我乐趣的源泉,更是我探求未知的起始。每当春天到来时,岸边的迎春花总是最先开放,一串串小朵嫩黄,簇拥生机,甚是惹眼。等到桃红梨白时节,我便偷出家里的掘锄子,拿在身后,跑出后门,沿着河岸往上走,手里挥舞着掘锄子,当刀使唤,乱砍着长得高的蒿子和不知名的花草;看见蹁跹飞舞的蝴蝶,就立刻扔了掘锄子,脱下轻薄的外套,抓着外套的一头,扑打追赶,就是逮不着;等我停下,不再追赶,不一会,蝴蝶却停在花朵上休息,我便将外套展开,蹑手蹑脚的挪到近旁,猛地一捂,蝴蝶便被我扣在外套下,我慢慢揭开外套,有的蝴蝶趁机而逃,那些没来得及逃的,被我捏着翅膀,放进口袋。之后,我才感觉到大拇指和食指有滑腻的感觉,原来两指上沾满了蝴蝶的鳞粉。 我就这样一路挥舞着掘锄子,扑着蝴蝶,挖着甘草,掏着螃蟹,采食着草丛中的蛇莓果,不知不觉就到了河流的源头。原来小河发源于村上机井的冒眼,和机井周围泥沙的渗水。我们村子,地下水源丰沛,听父辈们说以前是种水稻的地,水位高的地方自然会有水冒出来,而在水位高的地方,村上还打了机井,小河便比之前更显丰腴了。后来我才明白,这条小河最大的功用是灌溉农田。每当夏日干旱,村人就堵堰截流,引水入田,滋养作物。等水渗入泥土,田地水道里有时候便会有不少乱跳的小鱼。原来庄稼地里不但能收获庄稼,也能收获小鱼。每当这时,大人们就让我们这些在地头打闹的娃娃,抓起小鱼放进河里。大人们可不懂什么生态平衡,只是出于本能的对生命的敬畏,看着他们在地里挣扎,心有不忍,或者还因为鱼太小,根本不能吃。大人们的这些举动,使我们在以后抓鱼的时候,不捉小鱼,不捉肚内有鱼子的鱼,不把鱼一网打尽。 小河在我心智未成之时,便给了我三个世界:岸边的草虫世界;水面的倒影世界;水中的鱼虾世界。给了我接近泥土、接近生命、接近本真的机会和条件,催生了我追寻、认知、发现、想象的能力。 二、村北城壕 村子北头有一个城壕,是以前的护城河,那时年代慌乱,土匪恶盗横行,打家劫舍的事,时有发生,于是相邻近的几个村联合起来筑起一座高墙,墙外挖渠注水,设为城防,以保墙内各村的安宁。我看到的城壕,不过是一个池塘而已。听奶奶说,我小时候最缠我妈,不让我妈下地劳动,而是一直陪着我,不然我就哭闹。那时,村人皆以土地过活,稍有劳动力的人都得下地劳作,我奶奶就抱起我说:“婆抱我娃去城壕看水牛去。”一听这话,我就立即停止哭闹,乖乖地随我奶奶抱着走向城壕。我站在城壕的边上,看水牛在水中游泳,悠闲而自在,我能看整整一个下午,不哭不闹。 我以后独自再来看时,才发现这里寂静非常,水面宽十几米,不仔细看,根本感觉不到水在流动,水面浑碧,深不见底,岸上有老柳,树身上长满苔藓,一直延伸到树下的地上,踩上去绵软而湿滑,水中野草疯长,岸边芦荻比人还高,让人顿生岑寂寥落之感。我在想奶奶给我讲的那些土匪抢粮和财物的事,还有村人智斗强盗的事,继而我又会想到:这水中是否有什么洞府,洞府中有没有住着鲤鱼精、泥鳅精之类的灵怪。这些想法在不久后就得到了证实。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的午后,树上的蝉在聒噪,邻居家的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海叔、立鲜哥,要去城壕边钓鱼,我自然也要跟着去。城壕边上如常一样,四寂无人,我看他们给鱼钩装上蚯蚓,找好钓鱼的窝子,用鱼竿比比远近,再把鱼线抛进水里测测深浅,然后拉上来,根据浮标吃水的程度,再调整浮标的距离,再次扔回水中,最后蹲下身来,静候大鱼上钩。我之后这钓鱼的技巧和心态,尽得小海叔和立鲜哥的真传,如今试来,依然不减当年。 不一会就有鱼上钩,先上钩的往往是些小鱼,小鱼就像小孩子,容易被美食诱惑,而大鱼是不会轻易咬钩的。待到黄昏时候,小海叔的鱼竿的浮标有规律的动着,而竿尖的摆动深沉有力,节奏慢,竿尖下弯的速度慢而有力,经验告诉我们大鱼要上钩了,关键时刻小海叔立刻站起身来,快速顺水遛着鱼线,拉到岸边,借着岸的斜度将鱼拉到了岸上草丛,接着贴着地面又往前拉了一段距离,以保证离池塘远一些,这一连串的动作,皆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,目睹这娴熟的技巧,对小海叔崇拜不已。再仔细一看那蹦得无力的鱼,背青腹白,是一条比筷子还要长的鲤鱼。果然是鱼精啊。 农村那会鱼竿都是自制的,质量很差,若当时直接将鱼猛拽出水面,不是鱼线挣断,就是钓竿折断,或者大鱼脱钩,钓上来的几率很小。小海叔先借助水的浮力遛鱼,遛到岸边再借着斜坡的拖力把鱼顺上岸,然后再往远处托,以免大鱼在岸上挣脱,重又蹦进水里。 我们将鱼从带倒钩的鱼钩上卸下,用长草穿鱼鳃而进,从鱼嘴而出,提着大鲤鱼,收竿回线,在夕阳的金辉里,满载而归。 城壕岑寂荒静,充满时光沉积过的岁月感和历经变迁中的沧桑感,如一位老者深邃而充满故事,拥有着令人神往的丰富内涵。我猜不透它的内里到底蕴藏着多少生命和秘密,想不明它承载着多么厚重和苦难的村庄历史。然而过去的已经过去,只有这仅存的越来越小的老城壕,依旧藏聚着旧时的老风水。 三、耿峪河 我很小的时候,就已经有孔老夫子临水而望的习惯了。我虽然经常临水而望,也想过很多的问题,却从未领悟到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的哲思。 说起临水而望,就不得不说到一条河。在我家东边紧挨着的是冯尚坡村,冯尚坡村的东边一条大河蜿蜒而过。这条河名叫“耿峪河”,她发源于秦岭北坡七十二峪之一的耿峪。这条河的源远,自然流长。耿峪河流到冯尚坡村东边的时候,已经处于中游了,因为河里是细沙和小石,既不像上游尽是大顽石,赤脚走动,垫得脚底板生疼,又不像下游尽是淤泥,一脚踩下去就深陷其中,难以自拔,弄得满腿乌黑。在这里下河,腿脚不仅不会深陷下去,而且还会感到绵软舒服。 耿峪河河岸高,最高处有七八米,从而保证了发大水也不会漫过河岸。河的两岸种植着杨树,俊秀挺拔,茂然成林,春风夏阳里,丰姿尽展。树下野草葳蕤,时有野雉鸣于深草里,只能闻其声,却不能确定藏身之处,正寻思间,忽从你面前低飞而过,你心里一紧,还没来得及看清楚,又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杨树林的后面是一家挨着一家的瓜果园,有种西瓜的,有种梨瓜的;有种着苹果的、梨的、桃的、杏和李的。一到夏天瓜满地,果满枝,青红白黄,香飘四溢。 在春夏季节,河水不会很大,也不会充满整个河床,没有水的地方尽是白净的鹅卵石和细沙,这样就在河床的两边形成两道白色柔顺的带,陪伴着碧清柔美的河水蜿蜒而来又蜿蜒而去。河床有些起伏不平,于是就形成浅水深水。水浅的地方,一般一尺左右,我们常常脱了鞋子,拿在手里,顺着河床往上走,一边用脚激起清凉的水花,一边用手捏着圆薄的石片在水面上打着水漂,时不时还有莽撞的鱼,撞到我的小腿。等到走得累了,就躺在水边白净的石头上,仰面望着碧蓝蓝的天空,经常会碰到水鸟轻捷地从头顶飞过,叫声清脆悦耳,我一直看着它一点点消失在远方天空。天空任鸟飞,天空因鸟的存在而灵动,鸟因天空的高远而自由。飞翔,是一件多么干净的事啊。我欣赏着鸟儿飞翔,梦想着自己也要有一对自由的翅膀。 在水面开阔的地方,时常会碰见几只小野鸭由一只大的野鸭带领着浮在水面上。这些野鸭头上长着翠灰色的绒毛,眼睛像黑宝石一样,亮晶晶的,颈上有一圈灰白色的羽毛,好似灰白色的项圈。它们悠闲自在地慢游着,突然潜入水底,迟迟不上来,在你正思忖的当儿,却在不远的地方猛地浮出水面,嘴里叼着鱼,然后仰起脖子,几下就吞进肚里,然后又悠闲地慢游着。绿水悠悠,倒映着蓝天白云,野鸭慢游在水中,却似漂浮在天上。 不远处传来妇女们洗衣服的捶布声,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和激水声。于是循声而望,一群妇女在浣洗衣物,身旁的孩子挽着裤管在戏水、捉鱼虾。还有一些孩子,身上光溜溜的,一个猛子扎进深水里,潜到远处才把头露出水面,缓一口气,接着又钻了下去,几次三番之后,便不再潜水,而是在水面上游出各种花样,活像一条条无拘无束的鱼,自由自在的游弋在这清凉的碧波中。 在河底兴尽之后,重又回到高岸上,临水而望,目光一直追随着流水伸向远方,思绪也随之伸向了远方。水无常形,亦无常式,无拘无束,无尘污垢。泽万物而不居,历千年而不怠。穿顽石,劈高山,走地经,穿络脉,沉浮日月,吞吐八荒。止水静以致远,江流奔而入海。先民临水而居,生存、繁衍、发展,以致创造出文明。老子说:“上善若水”,的确是这样啊。 当西边落日的余辉透过岸边的杨树林,细碎的洒在河里的时候,我便该归家了。耿峪河优雅的风貌,便从我的眼里,流进我的心里,之后,我看到过很多的河流,却始终没有它让我如此的记忆深刻。在不知不觉间,它不仅成了我精神世界的塑造者,也成为我精神的依托。 声明:本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aoyae.com/dypz/8121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紫砂壶交流群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